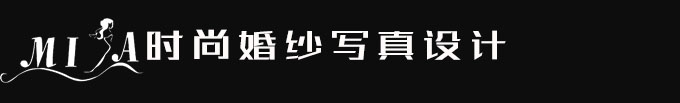- 邮箱:
- admin@eyoucms.com
- 电话:
- 0898-08980898
- 传真:
- 0000-0000-0000
- 手机:
- 13800000000
- 地址:
- 海南省海口市
●在海拔4600米的西藏那曲尼阿底遺址,考古人員發現了青藏高原目前已知的最早細石葉技術遺址。這一發現,証實了人類在距今約4萬至3萬年前,已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區
●証據表明,青藏高原從漢晉以來一直到隋唐時期,曾經有過若干條重要的交往線路,可稱為“高原絲綢之路”
●三星堆可以與世界對話,進行文明互鑒。過去,具象藝術在中國青銅時代很少有發現,三星堆的青銅器有神樹、眼形器、太陽輪形器等很多具象表達,恰恰與西方用具象藝術表達崇拜一致。
四川大學文科杰出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旅游學院、考古文博學院)學術院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國家重要人才計劃入選者,四川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主任。長期從事中國考古學的研究與教學,主要方向為漢唐考古、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學與藝術史、中外文化交流等,曾在西藏考古調查取得重大成果。發表論文200多篇,出版專著30多部,曾榮膺2022年度“最美退役軍人”。
人類是何時登上青藏高原的?農業是何時誕生的?文明又是何時才有的?最近幾十年,考古工作者不斷在西藏展開考古調查和發掘,叩問高原歷史。四川大學文科杰出教授霍巍就是較早挺進西藏展開考古調查發掘的學者之一。
在西藏工作期間,霍巍和同事李永憲在西藏考古中發現了細石器、西藏最大的佛教石窟皮央和東嘎石窟遺址,還發現了《大唐天竺使之銘》唐碑,証明唐代使節王玄策前往古印度的路線是從唐蕃古道經過高原的。
2025年9月中旬,霍巍接受了四川日報全媒體“文化傳承發展百人談”大型人文融媒報道記者的專訪,展開了中國考古尤其是西藏考古的神秘畫卷。
2022年,霍巍榮獲“最美退役軍人”稱號,大家才發現這位總是身姿挺拔、精力無限的考古學者,還有一段從軍經歷。
霍巍的父母都是軍人。在軍隊大院裡生活過的經歷,讓他選擇了參軍入伍。“在昆明集結時,才知道要去的是邊防部隊。坐了5天大卡車,才到了中緬邊境。”一年后,霍巍當上了班長。部隊的錘煉,為他后來從事需要團隊作業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1978年,霍巍等來參加高考的機會。他的主要復習時間是大家晚上休息以后。所謂復習也沒有任何資料,能接觸到的書籍很少,不過有兩本地圖集。好在霍巍一直保持很好的閱讀習慣,成功考上了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穿著軍裝、背著鋪蓋卷走進四川大學的情景,在40多年后仍歷歷在目。“那時大約凌晨6點,天還沒有亮,但校園裡已是一片讀書聲。”置身其中,霍巍感覺到一個新的時代已悄然來臨。
在大學期間,霍巍和同學們一樣,有一種爭分奪秒的拼勁。“我們出去考古實習的時候,不管是在大街上還是在車站裡,只要有點時間,就把背包當板凳開始看書。”
研究生畢業后,霍巍以優異的成績留校。他曾作為四川大學1984級實習團隊的指導老師,在1986年參與三星堆遺址的田野發掘,獲取大量標本。但最重要的經歷,還是第二次文物普查時在西藏的一系列工作。
當第二次文物普查開啟時,嚴重缺乏考古力量的西藏向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尋求幫助。消息傳來,霍巍和李永憲主動報名。此前,四川大學教授童恩正已在20世紀70年代帶隊參與西藏的第一次科學考古發掘,發現在世界上有重要學術影響的昌都卡若遺址,“這讓我對西藏非常向往。所以我一直在想,找機會踏上高原。”
出征前一天,在成都新南門的一家小館子裡,霍巍和李永憲每人點了一份粉蒸肉大快朵頤。
20世紀90年代的西藏,條件相當艱苦。霍巍和同事先是被派去日喀則最遠、最偏僻的4個縣,此后相繼轉戰山南和阿裡地區,用腳丈量了西藏的一大片土地。
他們在穿越千裡無人區時,因汽車顛簸,機油滲進米袋,為維持生計,吃了好長一段時間帶機油味的米飯﹔沒有蔬菜,脫水的干菜味同嚼木,難以吞咽。高原很多地方沒有路,他們碰到過泥石流、塌方,汽車還曾陷進河中險些翻車。“那時候,大家很自覺地首先搶救相機和膠卷,再爬出車窗逃到岸上。”到現在,他們的很多調查記錄本都能看到河水浸泡的痕跡。
壯闊神秘的西藏,很快回報給霍巍和李永憲重大的考古新發現。1991年,他們在西藏日喀則靠近邊境的吉隆縣,發現迄今為止中印交通線上唯一的一通唐碑——《大唐天竺使之銘》。
入藏前,霍巍一行對西藏地區既往的發現史、研究史有過專門了解,大致明白了可以突破的重大問題的方向。“例如,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活動,以往大多通過地質學家地表採集石器作為標本。我們進入高原后,就有意識通過實地調查去發現這些人類早期遺存。沒想到,1990年,就在雅魯藏布江的中游地帶,一舉發現了30多處石器地點。”到了吉隆縣,霍巍根據史料記載,推測有“大唐第一猛人”“一人滅一國”之譽的唐代使節王玄策出使古印度的交通路線,極可能經過此地。因此,他們格外用心地四處尋訪相關痕跡,線索很快主動上門。
1991年6月,吉隆縣委副書記帶來一個線索,在宗嘎鎮阿瓦嘎英山腳下,有一塊石頭上刻了漢字。“老百姓對這通刻字石頭相當尊重,挂了哈達、涂了酥油。但當時這塊石頭所在的位置要修水渠,因此縣裡希望我們能去看一看。如果不重要,修渠時就會把石頭炸掉。”霍巍和李永憲次日趕到現場。他燒了一桶開水,洗去上面的酥油。這一洗不要緊,石碑上率先露出篆書陰刻的“大唐”二字。霍巍心裡一喜——這是唐代的碑!他的大腦裡頓時浮現出“王玄策”3個字。
王玄策,唐朝官員、外交家,數次出使古印度。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跡是,貞觀二十一年(647年),以正使身份前往古印度。此時,阿羅那順成為中天竺的新國王,派軍隊劫掠使團。王玄策調吐蕃兵、泥婆羅兵擊敗阿羅那順,民間稱其“一人滅一國”。
霍巍不斷沖洗著碑刻上的酥油,“天竺”“大唐顯慶三年”等更多文字重見天日,果然是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古印度時所刻的石碑。
碑文顯示,王玄策當時的官職是左驍衛長史,路經此地時恰遇洪水,道路不通,不得不搶修棧道。回想奉命遠道出使,於是在此刻石勒銘以顯大唐聖威。碑文還提供了很多有意義的線索,如王玄策的使團組成明確為函谷關內的良家子弟,他的兒子和一個侄兒也在隊伍中。“史料記載王玄策為虔誠佛教徒。此次西行,既要完成大唐使命,也要帶著家人實現向西天求法的美好願望。”這通碑刻,雖然因多年風化侵蝕嚴重,且下半截因長期埋於土中已經蝕毀,但仍存的200多字,足夠揭示王玄策出使天竺的歷史事實,且此碑比大昭寺前所立的《唐蕃會盟碑》早了100多年。這通在中印交通線上迄今唯一考古發現的唐碑,對進一步研究古代唐蕃、中外關系等問題意義重大。2001年,該碑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2年,霍巍又有了新想法:能不能找到佛教傳播路上的石窟寺?在他看來,西藏周邊都是佛教流行的地區,不管是新疆還是中亞抑或中國西南地區,均有大量的石窟寺遺存。尤其在南邊,印度還是佛教藝術的發祥地。但在1992年以前,西藏沒有發現一處與敦煌莫高窟相似的佛教遺存。“這種現象極不科學。”疑惑在他心裡一直不散。
1992年夏天,霍巍一行在阿裡展開文物調查。每到一處,他都習慣性地和當地人聊天征集文物線索。
皮央和東嘎是兩個自然小村落,相距約兩公裡。一天,在從皮央向東嘎行進途中,路上一位牧羊的小姑娘揮手示意搭車。待女孩上車,霍巍照例問她有沒有見過一種畫了畫的洞子,沒想到她說:“看到過,因為下雨的時候我喜歡把羊趕到洞裡避雨。”
霍巍內心一陣狂喜,立刻請求小姑娘帶隊前往。從緊鄰皮央村西側山崖一路向上攀爬,在接近山頂時,小姑娘指著一處洞窟說:“到了。”
此時,日近黃昏,霍巍順著方向一望,恰好一抹斜陽打在石窟上,滿目丹青!那一刻,霍巍恍如置身敦煌大洞窟。視覺上的極度震撼與發現石窟的喜悅交織在一起,讓他激動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在此后的日子裡,皮央和東嘎石窟遺址一共發現3座繪有精美壁畫以及存有彩塑的石窟。長期以來西藏沒有發現石窟壁畫的歷史,就此被改寫。
這處遺址,是西藏考古迄今已發現的最大一處佛教石窟遺址,為西部地區佛教藝術的傳播提供了重要資料。它的發現,與新疆、河西走廊、中原地區以及西南地區的石窟一起,形成環狀分布,填補了佛教傳播鏈條上的缺環。1994年,西藏文物局與四川大學聯合調查隊再度前往阿裡,維修並再次調查了皮央和東嘎石窟遺址。2013年,皮央和東嘎石窟遺址成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回首過往,霍巍認為這些重大發現偶然中存在必然。“如果我沒有准備,在西藏沒有認真尋訪,可能機會就擦肩而過。當有了准備,或許重大的發現就會突然而至。”
霍巍如今依然奮戰在教學一線,在高原絲綢之路研究以及用考古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和源方面不斷探索,成果豐碩。
霍巍: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西藏地區的考古調查工作主要是外國探險家、傳教士以及部分學者在從事,資料非常零散。人類何時征服青藏高原、何時在此定居、何時有文明史等,有很多謎團待解,這也是全世界都共同關心的學術問題。
過去,藏文的歷史文獻中關於這些話題倒是有不少神話傳說,但並不能作為証據。考古發掘,可以把這些涉及人類文化和文明產生的重大歷史講清楚。從這個角度而言,在青藏高原上展開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意義。青藏高原何時有了人類?通過一代又一古學者的努力,我們已經知道,至少在4萬年前,人類就已征服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帶。
在海拔4600米的西藏那曲尼阿底遺址,考古人員發現了青藏高原目前已知的最早細石葉技術遺址。這一發現,証實了人類在距今約4萬至3萬年前,已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區。
這處遺址是人類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存,也創造了人類挑戰與征服高海拔極端環境的新紀錄,對探索早期現代人群挑戰極端環境的能力、方式和遷徙、適應過程,研究西藏地區人群的來源與族群的形成等,具有重大意義。
何時有了農業?通過四川大學參與發掘過的西藏昌都卡若遺址等,我們可以知道,至少在距今5000年前,青藏高原已經誕生了農業。卡若遺址是一處距今5300年至4300年間的新石器時代重要聚落遺址,發現了半地穴式房屋、地面石砌建筑遺跡以及陶器、石器及粟、豬骨和投擲石球等,說明當時已擁有農業和畜牧業共同發展的生產經濟方式。
青藏高原腹心地帶一直被認為是生命禁區,人們很難想象這裡會產生高度發展的文明。但通過距今約3500年的西藏曲貢文化遺址,我們可以看到,青藏高原人群在當時已經開始制作金屬器。這裡出土的銅鏃,經鑒定為銅錫合金,証明當時此地青銅冶鑄已有相當的發展。由此可以推斷,當時這裡已進入青銅時代。
曲貢文化遺址春秋時期的石室墓中,還出土了帶柄銅鏡,其上陰刻了牦牛形象。証明當時青藏高原腹心地帶的人群,或許已經馴化了牦牛。
根據現有的種種考古成果,青藏高原地區的文化史,並不比我們想象的要晚許多。這些發現,對認識青藏高原的人類史、文化史和文明史,具有重要意義。
霍巍:根據現有的材料來看,有可能是人類從周邊低地逐漸向高原擴散,路線也不一定隻有一條,可能包括川西北高原、青海、甘肅等通道。海拔3750米的四川稻城皮洛遺址,可能就是行進線路上的遺存之一。而它的年代,距今至少在13萬年以前。
位於青藏高原東北部、海拔3200多米的甘肅白石崖溶洞發現的人骨化石,証明了古人類種群丹尼索瓦人在距今約19萬年至3萬年裡,曾長期生活在青藏高原。
記者:您提出的“高原絲綢之路”概念備受學術界關注。有哪些証據証明高原上存在這樣一條線路?
霍巍:絲綢之路的概念最早由德國學者李希霍芬提出,此后衍生出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各種提法,但這些線路都沒有提到青藏高原。到西藏開展相關考古工作后,我發現西藏不是一個與外界隔離的孤島,反而與外界有非常密切的聯系,在考古學上也有很多証據。
例如《大唐天竺使之銘》,用實物材料証明從中原通過唐蕃古道,經過拉薩,可以抵達今天的中尼邊境,再進入印度境內。
我的學生們后來在阿裡地區發現的漢晉時期故如甲木墓地,其中不僅出土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絲綢,還發現了茶葉狀殘渣。史料記載,文成公主進藏時,首次給西藏地區帶去了茶葉。但這裡發現的茶葉,比文成公主時期早了幾百年。這些絲綢和茶葉的發現,顯然說明高原上存在一條“絲綢之路”,並且至遲在漢晉時就已開通了。
這些年,考古人員在青海、西藏等地考古出土了很多絲綢,有的帶有連珠紋、對馬對獸紋等當時在中原地區和邊疆地區都很流行的一些紋樣,有的絲綢還不排除是在成都生產的。同時出土了不少金銀器,造型、器類和裝飾紋樣、鑲嵌寶石的風格,都與絲綢之路沿線上的中西亞地區的發現可以聯系起來。西藏腹心地帶羊卓雍湖旁,還發現了波斯薩珊王朝的錢幣。
這些証據表明,青藏高原從漢晉以來一直到隋唐時期,曾經有過若干條重要的交往線,可稱為“高原絲綢之路”。這條絲綢之路穿越青藏高原,連通了中原地區、西域、中亞和南亞,功能和意義都非常重大。
霍巍:高原絲綢之路架起了西藏地區與中原地區交流、交融的橋梁,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上意義重大。事實上,青藏高原近年來的諸多考古發現,都能証明這一區域早在數千年前就已經開始和東邊進行交流。
例如卡若遺址,出土的小米應該傳自甘肅馬家窯文化,禮儀性質的不少玉器來自東邊,半地穴式建筑與中原地區的半坡文化、馬家窯文化的居住方式一樣,陶器與黃河上游地區甚至川西北高原出土的十分接近。再如曲貢文化遺址,青銅和鐵的金屬器很可能受到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區域的影響。這些區域可能為他們輸送了工匠,也可能是輸送原材料的重要基地。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西方學者認為西藏和中原並無聯系。對這樣的論斷,如果僅依靠晚到7世紀左右的藏文文獻,顯然不能解決西藏早期的問題。
我們說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藏族先民在內的西藏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西藏的歷史和文化,從考古發現的當地先民的生產工具、生活方式、食物體系等,完全可以証明,西藏與東邊的這種交流、交融,從史前就已開始並長達數千年。
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最首要的問題是要正本清源。今天我們深入挖掘、整理和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可以清晰地看到西藏各民族有史以來就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任何力量也從未讓他們分開過。今天我們要講好中國故事、講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故事,這些考古成果就具有重要的價值。
記者:您曾帶領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師生參與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輪考古發掘。在您看來,三星堆的價值有哪些?
霍巍:三星堆毫無疑問是世界級的考古發現。首先,它是古蜀文明的輝煌創造。甲骨文中的蜀以及早期文獻《尚書》提到的蜀究竟在哪裡?幾千年來沒人說得清楚。三星堆經過兩次發掘發現了8座祭祀坑,可以看到它有非常發達的青銅文明,向世人展現了極具特點的青銅文化。
其次,三星堆不是孤立發展的青銅文化,跟中原的夏、商、周都保持了密切聯系。三星堆的鑲綠鬆石青銅牌飾和河南二裡遺址出土的幾乎一樣,大量玉牙璋、陶盉的樣式跟二裡頭的相似,而二裡頭時期就是夏王朝時期。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中,出現了非常明確的商代中原地區的青銅禮器尊和罍,說明三星堆借鑒了中原這些器物進行祭祀,與中原青銅禮制息息相通。這些尊和罍不僅造型、紋樣與中原地區及長江中游的相似,而且成體系,不排除技術、工匠都受到中原影響。
但三星堆之所以神秘,在於古蜀先民有自己的一套青銅禮器。包括神樹、可能是祖先神或別的神的面具,還有代表了當時西南地區眾多人群的形象,可以看出三星堆已經具有廣闊疆域,發展到了王國階段,它們和文獻記載相互印証。這套用動物、神山、神樹輔助祭祀的傳統,《山海經》《楚辭》等文獻曾記載中原地區也曾有過,但迄今沒有實物出土。三星堆保存了這套非常完整的祭祀系統,彌補了中原地區與古史記載相互呼應的缺失。
再次,三星堆可以與世界對話,進行文明互鑒。過去,具象藝術在中國青銅時代很少有發現,三星堆的青銅器有神樹、眼形器、太陽輪形器等很多具象表達,恰恰與西方用具象藝術表達崇拜一致。大家能看得懂三星堆,自然就有利於和世界文明進行對話。
霍巍:我認為有兩大類別:一是祭壇,另一個就是神靈動物。大家在三星堆博物館可以看到研究性還原的青銅神壇,細致入微地刻畫了三星堆的祭祀場景。尤其是祭祀的平台在一隻神獸上,這體現了古蜀高台祭祀的傳統。考古工作者此前在成都羊子山發現過一個土台遺跡,由此可以推測,古蜀人祭祀非常崇尚高台。可能他們覺得高台離天很近,在高台祭祀更有利於人神、天地之間的溝通。
三星堆還有一批神靈動物,如有翅膀的龍,有的龍是羊頭或虎頭等。這些動物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是古蜀人為了讓它們能輔助參與祭祀、溝通神靈而創造出來的。動物長上翅膀,寓意可以把人帶到天上,向祭祀對象表達敬意。
當然,龜背形網格狀青銅器要特別推薦。它應該是古蜀人在祭祀中用來通靈的重要器物。只是,怎麼使用、為何中間還夾有玉石等,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霍巍:考古、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可以做的有很多。例如考古,三星堆的王陵、青銅冶鑄的作坊、宮殿區、祭祀的第一現場等都還沒發現,期待未來展開工作。此外,三星堆象牙、海貝從哪裡來,三星堆人是怎麼認識這個世界的,為何會形成現在的祭祀坑等謎團,也期待多學科綜合攻關,甚至可以引入人類學、神話學等學科參與,去理解當時三星堆人的信仰和審美。
目前,三星堆考古發現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還能看到更多的新發現。
霍巍的工作重點並非職業考古,教書育人、學術研究才是主業。約請採訪他時,他的工作安排相當緊張,最終同意擠出一個半小時給我。時間一到,立刻結束,如同老師下課。在我們收拾拍攝器材時,他已經把在外等候的學生們喊進來開始上課了。
這樣一位既要傳道授業,還要在考古研究領域耕耘的學者,幾十年來視考古事業如生命。除了多次前往西藏,在稻城皮洛遺址、三星堆遺址、鹽源老龍頭遺址等考古發掘現場,他都以專家名義前往考察。
尤其在三星堆,他不僅大力推動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師生參與考古發掘和研究,更在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等不同的場合,不遺余力地宣傳推介古蜀文明。對三星堆的價值意義,他站在世界文明比較研究的高度進行審視,對公眾理解三星堆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對西藏地區的考古發掘,更是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角度提煉其意義。
這正是考古的價值所在,也是文科存在的重要意義。以霍巍為代表的一批考古人,以考古材料和嚴謹的研究,為國家的文化傳承與文明溯源,提供了科學依據。為國家和民族“辯經”,考古人以實際成果體現了他們的文化自信和擔當。
相信以霍巍為代表的考古人,未來將以更多的成果,印証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增強民眾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展示文科的力量。

人民日報社概況關於人民網報社招聘招聘英才廣告服務合作加盟供稿服務數據服務網站聲明網站律師信息保護聯系我們
人 民 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版 權 所 有 ,未 經 書 面 授 權 禁 止 使 用